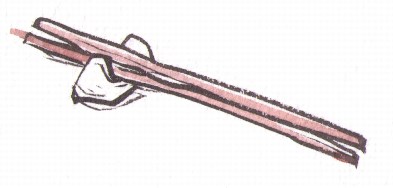我的小田園
廚娘變農婦,一個女作家的耕食日記
2015/08/03
- 文字 / 蔡珠兒
暌違七年,烹作美饌的文藝廚娘蔡珠兒又有新書。這次,她在罹癌後,直接走入食物的最源頭,成了為後院的菜苗蔬果們,時時刻刻牽腸掛肚、沾染滿手泥濘的自耕農婦。
在香港要擁有個可遠眺海景的後院,可以說得上是「奢華」。許多人就選擇挖個泳池,時髦一番。偏偏蔡珠兒卻篤定的說,她就是要把地拿來種田。
這傻勁,讓蔡珠兒兩年來,一點一點在自家後院慢慢挖,撿出的磚石廢瓦,可以裝滿幾隊砂石車,而她曬黑、中暑、被蚊蚋狂咬、割傷破皮、手上起繭、腰痠臂痛,甚至讓左臂患了「網球肘」……。
然而那些勞心勞力,卻也幫助蔡珠兒從這幾年患癌、作治療的辛苦過程之後,有機會靜下心來,透過與自家後院的那一畝小田園相處對話,透過發現生命變化的驚喜滋味,重新找回生活活力,以及生命的各種可能性。(文‧陳乃菁)
菜田有條龍
治療結束,不必每天跑醫院了,我歡天喜地,像刑滿出獄,領回生活重獲自由,時間不再割裂破碎,每天又是完整一大塊。還我河山,歸去來兮,第一件事,就是耕田整地。
幾個月沒理,菜園蓬頭垢面,滿目瘡痍,田畦被暴雨沖得歪七扭八,泥壤流失,露出石礫,荒涼得像戈壁。田裡亂草如麻,地瓜葉粗老,空心菜開花,落葵憔悴黃瘦,半枯的南瓜藤牽纏絆掛,邋遢不堪。
我摧朽拉枯,去蕪除穢,大力揮鋤掘地,覺得痛快極了。手術後不能勞動,電療期要避免流汗,也不能幹體力活,綑手綁腳的,憋得真慌,現在終於解禁,可以大刀闊斧,盡情揮灑,一隻蟲又成一條龍,我渾身力氣,勁道十足。
但這地,比我更有勁。鋤頭翻起地皮,砍進泥肉,正想得寸進尺,軟土深掘,卻遭受反彈抵抗,碰頭撞壁,趑趄不前,鋤尖鏗鏗作響,吃不消哀哀叫。鋤到石頭了,我彎腰想撿出,卻無法動搖,那東西烏黑粗硬,深沉厚實,簡直是長城。
正面難以攻堅,我從側面包抄,用鏟子把周圍挖深,刨鬆後撬起,果然是一堵水泥牆,臉盆大,兩手才搬得動。咦,去年翻土整地,已經清出幾噸磚瓦廢料,這塊是漏網之魚吧。我安慰自己,繼續鋤地,可是沒多久,鏗鏗聲捲土重來,更加淒厲不祥。
天啊,這下是我慘叫,怎麼又來了?往下才挖幾公分,斷垣殘壁陸續出土,破瓦碎磚,石頭水泥塊,鬱鬱磊磊,遍地坎坷。我楞在那裡不敢相信,去年明明清乾淨了,怎麼又冒出來?天老爺啊,難道石塊廢料也像番薯,會在地底繁殖蔓生?
真是氣傻了,這事叫天有什麼用,只能喚地,不,應該捫心自問,怪自己功夫不足。地裡肯定不會長出石頭,但土質如此磽薄粗惡,遠出意料,只怪我經驗不足,整地不夠力,耕得不徹底,瓜菜飄在淺土,難怪長不好。
於是揮鋤舞鏟,挖地撿石,又像去年一樣,弄得摧背折腰,指掌起繭冒泡。幾坪大的菜園,搞了大半個月,一路往下掘,磚石還是沒完沒了,周而復始,徒勞無功,簡直像薛西弗斯的神話,他是推,我是撿。不成啊,哪有那種希臘時間,冬至已過,播種要來不及了。
挖到二十來公分,我決定罷手,這深度不能種蘿蔔,種葉菜綽綽有餘,盡夠了,下一季接著挖吧。這回還得吸取教訓,打好基層肥底,我把兩桶養了半年的漚肥倒進田底,拌進草木灰和牛骨粉,掩埋好,悶幾天又曬幾天,然後翻動耙鬆,分畦劃畛,闢出新菜田,這下總該肥滋滋了。
文蒂在疏苗,清早送來一籃菜苗,有芹菜、青花菜、蒜苗,齒葉和捲心兩種萵苣,趁著晨光熹微,我趕緊拿去種。菜苗荏弱軟嫩,吹彈得破,要輕拈細挑,嵌進土中,用指頭暗勁摁實;我小心翼翼,還是折斷兩株捲心萵苣,這菜簡直一碰就酥。鋤地要大力,種菜用陰力,剛柔相濟,文武交加,不簡單咧。
菜苗都活了,原本丁點大,幾乎看不清,幾星期下來,綠意逐漸暈染擴大,生氣勃發,新潤可喜。呼呼,這一季歷盡折騰,總算吊車尾,趕上冬耕了。
老蔡種瓜
身長七十三公分,體重七公斤半,見到的都來掐一掐,抱一抱,呵呵,我說的不是小孩,是我種的瓠瓜。
晚春種下瓠瓜苗,有兩株欣欣向榮,攀枝引蔓開了花,到了夏末,卻突然枯黃萎死。我心痛不已,趕緊亡羊補牢,拿出在建國花市買的瓜種,一口氣全播了,菜園籬邊種了十來株,剩下兩株,隨手插在前院。
真是有鬼,我拚命呵護下肥,菜園的瓜苗就是無精打采,瘦瘦呆呆,反倒是前院那兩株,抽高怒長,肥壯活潑,等不及搭棚,它已經來勢洶洶,一溜煙爬上九重葛樹籬,伸藤吐鬚,開滿碗口大的白花。
開了個把月,都是空包彈,浮花浪蕊不見結瓜,秋分已過,今年恐難修成正果,不過滿樹白花,和九重葛交織穿插,甜白縹紫相映,吃不到瓜,當觀賞花木也挺好。
有一天,鄰村的朋友打電話來說,哎,昨天開車經過妳家,那瓜愈長愈大啦。嗄,什麼瓜?我連忙出去看,鏤花欄杆纏滿樹藤,枝葉深處,赫然垂吊一瓜,小腿粗長,水綠皮色,瓜身有深長瘢疤,想是一路長,一路被九重葛的尖刺擦刮而成,披荊斬棘,勇猛可嘉。這就太奇了,明明瓜就長在門口,我們每天進進出出,怎麼會視而不見,渾然不察?
一不做二不休,四下張望,抬頭又發現一條,低垂沉墜,觸手可及,啊呀,不只,西邊和樹頂高處,也各懸一瓜,共有四條哩。這下樂壞了,每天醒來,就到前院視察看瓜,隔幾天還搬梯子去量長度,喜不自勝。瓜從一呎多長,漸漸豐肥長到近三呎,小腿變成大腿然後成了牛腿,比冬瓜還長,龐然高掛,連路人走過都駐足觀望,嘖嘖稱奇。
去查書,這品種叫斗瓠瓜,又叫冬瓜蒲,我從沒在菜市見過,也許瓜農不等它長成,趁嫩就採了。我當然捨不得摘,留在樹上繼續招搖,看看到底能長多大。
由秋入冬,瓜藤還在瘋長,張牙舞爪,漫天跳竄,霸高位搶陽光,九重葛正值花期,被惹毛了,也回咬反撲,奮力伸展枝條,甩竿般拋向半空,你高我更高。瓜葛牽纏,雙藤交戰,紫蕊白花披頭蓋臉,荊條枝蔓怒髮衝冠,為了養瓜,我也不敢整枝修剪,前院遂綠雲罩頂,枝葉低垂披面,猙獰刺人。這倒好,萬聖節鄰居扮鬼扮馬,我家不必扮,虯結撩亂,活脫脫就像鬼屋。
以前看楊萬里寫瓠,還道奇峭誇張,「笑殺桑根甘瓠苗,亂他桑葉上他條,向人便逞廋藏巧,卻到桑梢掛一瓢」,如今才知,誠齋兄有啥說啥,如實報導,極其正確傳神,他那瓠還偷偷摸摸上樹,我這株明目張膽,更狂啊。
但時不我予,瓠瓜怕冷,寒流一來就蔫了,藤葉枯敗如殘荷。我花了番功夫,採下四條大瓜,自留一條,其他分送鄰居──早有人跟我討了。
養了兩個月,還是牛腿長,皮色雖青,卻已木質化,刀槍不入,快要乾老成瓢了。可是瓜身直通通的,既長且窄,凹位平淺又沒把手,恐怕沒法子做水瓢。
原來《莊子.逍遙遊》裡,惠子說的那個「五石之瓢」,拿也拿不起,舀也舀不進,真的有這東西啊。
瓜擱在廚房,朋友來品評觀賞,存影留念,玩了好一陣,沒打算吃。但我忍不住好奇,終於把它剖了,皮殼粗韌如柴,瓜籽大得像花生,內裡的白瓤卻豐軟如綿,飽含汁液,應該能吃啊。家裡沒斧頭,我用菜刀奮力劈開,砍到手痛,終於把瓜剁成塊,下排骨、淮山和蓮子,煲老火湯。
沒想到,煲出來湯汁澄淨,有說不出的清甜,瓜肉也好吃,稠糯潤口,遠勝鬆泡泡的冬瓜節瓜。
惠子啊,難怪莊子要訓你,這大瓢能賞花能看瓜,玩了半天還能煲湯,哪是大而無當?
紅耳鵯度小月
種瓜既然得瓜,種豆也不差吧,播下豌豆,很快抽芽了,蜷曲翠綠,蓄勢待發。我買來竹枝,正打算搭籬架,卻發現豆苗斑斑點點,已給蟲子啃了大半。
啊呀,大冷天也有蟲?我趕緊蹲在田邊,火眼金睛大搜索,捉了好久,卻連蟲毛也不見,只好調了點辣椒水,到處噴灑,又摘了香茅葉,鋪在畦間驅蟲。第二天,好咧,剩下的一小半也沒了,遍地禿枝光桿,香辣豆苗給吃完了。
氣得牙癢癢的,問農友怎麼辦,莉姊來看過,搖著頭說:「唔係蟲,係雀仔囉,你在田邊掛幾張光碟,最好罩上紗網啦。」
原來是鳥啊,我聽了轉怒為喜,很是高興,太好了,鳥兒賞光來我家吃飯,哪裡捨得趕?歡迎歡迎,我趕緊再去撒籽種豆,給嬌客準備豆苗大餐,鳥兒吃剩的莖桿就做綠肥。草地菜園,可以招蜂引蝶,惹蟲邀鳥,只是我有分別心,厭蟲愛鳥,偏執不悟。看到鳥兒在園裡啄食,我總以為牠在幫我吃蟲,實則除了蟲子,鳥兒也吃別的。
喜鵲、八哥、柳鶯、鵲鴝、山雀和斑鳩,都是園中常客,我最愛看白鶺鴒,輕靈翩躚,尾巴一掀一掀的,細腳碎步,卻迅疾如風,快得像水滸裡的「神行太保」,見人偷窺,唧唧驚叫,波浪狀飛走了。
前院有盆四季桔,晚秋滿樹金豔,可是沒等到過年,已被白頭翁啄得七零八落。這果子酸,只能醃桔醬,白頭翁照樣吃得香,每天相揪拉隊,踞樹大嚼,吱喳嬉鬧,吃得滿地狼藉,隨後蟲蟻來舔汁,麻雀和綠繡眼來清皮渣,珠頸斑鳩來撿籽粒,傍晚紫嘯鶇也悄然來訪,縮著脖子,自飲自啄。我從廚房觀賞,看得入迷出神,差點把菜燒焦。
冬天糧少,要度小月,白頭翁不揀食,連嗆鼻的番茄葉都吃,但牠的親戚,抹紅頰梳龐克頭的紅耳鵯,可就挑嘴了。
莉姊說得沒錯,我觀察了幾天,發現豆苗是白頭翁的表哥紅耳鵯吃掉的,還有辣椒葉。我種了幾棵指天椒,長成灌木叢,椒果火辣,椒葉卻可口柔滑,這傢伙連葉帶芽,整樹啄得清光,難怪辣椒水也不怕。
然後是青花菜(綠花椰菜)。前陣子種的菜都長起來,青花菜尤其好,油碧肥綠,葉闊梗粗,我正巴望開花結球,紅耳鵯卻等不及,搶先來開飯,從早到晚每天吃三頓,把菜葉啄得坑坑洞洞,襤褸如破衫。
這小子嘴尖,田裡的韭菜、芫荽和芹菜,辛香濃烈,牠固然嫌棄不愛;生嫩的萵苣,軟厚的紅鳳菜,牠也聞都不聞,獨沽一味只吃青花菜。真識貨啊,牠知道十字花科的青花菜,跟芥蘭和菜心一樣,入冬經霜有甜味,特別鮮脆肥美,比起來,萵苣和紅鳳菜,就平淡索然了。
天上的飛鳥不種不收,天父尚且養活牠,呵呵,那麼種菜給鳥吃,就算替天行道吧。
莉姊和文蒂給菜田罩了網,鳥兒照樣趁隙找縫,鑽進去快意大啖,兩人納悶嘀咕,「咩今年的雀仔咁惡?」
新聞說,今年冬天,全球各地發現離奇死鳥,原因不明,可能死於冬寒、煙火、磁極變化,外星人或者世界末日。好邪啊,我們在田邊吱喳議論,好彩這裡的鳥還饞嘴肚餓,生猛得很哩。
不遠處,一隻紅耳鵯大剌剌啄著菜心,偏頭斜睨,面無懼色,因為牠知道,養活牠的,不是我們。
桃花與中文
去年天冷,香港鬧「桃花荒」,花給凍傻了,好久都掙不出,枝杈木頭楞腦,光禿禿的,豎在寫字樓和商場,一蓬蓬像倒栽的竹掃把。商家急了,居然在枝條黏上假桃花,掛滿銅錢和利市封,把那樹折騰得妖里怪氣,我看著可憐,走過總要遠遠繞開。
樹下倒熱鬧,有人擺出媚態拍照,有人繞著樹轉圈,催旺桃花行大運,祈求今年情場如意,人緣好,FB(臉書)和微博都人氣熱爆。哎呀,這我就用不著了,情場已打烊,人場有老友,二三子盡夠了,快些走,免得被浮花浪蕊濺到,沒的招煩惹惱。
桃花我是喜歡的,去年春節買了株,開完花種到園子裡,今年一月,開始含苞。我沒給桃樹剪枝摘心,所以枝條分杈不密,花也稀疏零散,開出來不是「一樹桃花千朵紅」,反而像梅花,星星點點,闌闌珊珊,不過花朵特別肥碩,密瓣嬌蕊,光豔照眼,而且居然有香味,湊近細聞,是種老式的胭脂水粉氣,有點像夾竹桃。
而桃色,那種義無反顧,深情痴迷,濃烈爛熟到快要滿瀉的粉紅色,要怎麼形容啊,唉,我這中文白讀了,站在花前,腦中如電光擊閃,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詩經,「桃之夭夭,灼灼其華」,然後就沒了,呆看半天,再也想不出更好的。古人厲害啊,寥寥數字,用了三千年也不磨損,還是鮮活傳神。
但只說桃花美豔,未免以偏概全,把它瞧扁了。牡丹富泰,水仙清雅,都沒啥好爭論的,桃花卻亦正亦邪,矛盾弔詭,可就複雜了,有時俗豔,有時清麗,一下子喜氣熱鬧,福壽無疆,一下子又孤絕淒冷,薄命不祥。
而且桃花是種狀態和概稱,就像「江湖」,中國人一看就懂,跟外國人就講不清。譬如桃花運,有一年,帶英國朋友琳去逛年市,看到維園處處桃花,琳十分好奇,我跟她說,這花象徵愛情和婚姻。「就像玫瑰嗎?」啊不,我趕緊補充,更多咧,還有人際關係,而且「桃花運」不一定可喜,弄不好,可能是「桃花煞」和「爛桃花」呢。
別說琳,我自己都似懂非懂。表面看來,桃花不是儒學老莊,對中文好像無關緊要,但骨子裡,它浸潤深沉,影響廣泛。不妨用「反證法」來觀察,如果像內地對付敏感詞,譬如茉莉花,把桃花從文化裡封禁抹消,那中文豈只失色,恐怕還會失血失重,休克昏倒。
桃花運,難道改成玫瑰運?杏眼桃腮,人面桃花,桃李滿天下呢?劉郎、武陵、小桃紅和桃花塢要怎麼辦?詩詞歌賦也完蛋了,元都觀裡桃千樹,竹外桃花三兩枝,可愛深紅愛淺紅,桃花流水鱖魚肥……,還不說桃葉桃枝哩。
李白春宴,劉關張結拜,也得另找地方,改去牡丹園或者竹里館。還有桃花源,這損失最慘重,春來遍是桃花水,仙境卻滅絕,桃源望斷無尋處,世外沒有烏托邦,只剩下荒涼粗礪的現實,真恐怖。
矛盾的是,桃花像櫻花,其絕美極至,不在於夭夭灼灼,怡情悅目,反在於生死蒼茫,由盛而衰,當落英繽紛,亂紅如雨,原本輕薄的審美,和時間空間發生撞擊,遂轉為深厚沉鬱,說是賞花,定睛端詳,卻乍見生命真相。
因此,寫桃最好的,詩經以降,我以為是張愛玲的《愛》,寥寥幾百字,白描淡墨,只說樹,連花都省了。「是春天的晚上,她立在後門口,手扶著桃樹。」看似寫景,忽然筆走龍蛇,刷刷刷幾句,那一生就這麼過了。時間無涯的荒野裡,只有那株桃樹。這篇我熟到可以默書,但每次讀,還是驚心動魄。
西蘭香芹
春寒料峭,青黃不接,鳥兒饑不擇食,連清苦的萵苣葉都吃,啃到只剩莖桿。西蘭花(就是青花椰菜)給啄得更狠,菜葉襤褸破爛,衣不蔽體,剩下梗子和葉脈,赤條條白森森的,有如貓兒舔淨的魚骨,本來裸體,現在露骨。
好在盜亦有道,鳥兒沒啄嫩芽,西蘭花雖然禿了,還是開始結花,芽心凝出蒼綠的小骨朵,我喜出望外,趕緊下追肥。天氣回暖,花蕾漸豐,但一直沒分檗,菜花似的就那一撮,沒長成圓胖的蕾球。想再等一陣,可時不我予,晴暖數日,側花開始泛黃,再不採就老了。
用手逐棵掐折,花梗瑩碧生脆,然而最粗的,只像珍珠奶茶的吸管,我特意折長些,因為莖梗比花蕾營養,而且更甜。三十幾株採完了,也就一小籃,零花散朵的,湊起來頂多一個蕾球,市場裡,三球西蘭花才賣幾塊錢哩。我這收成非但少,還整整種了三個月,成績實在太爛了。
可是我卻很高興。因為本來已把西蘭花「撇帳」,跟豆苗一樣,當成公益作物,種來餵鳥,不指望收成了,沒想到無中生有,由零變一,分外驚喜。我仔細摘洗,拈去蕊間的蛾繭,這菜還真難種,不是鳥就是蟲,天知道,市場那些肥碩的西蘭花球,到底下過什麼料?
該春耕了,我翻開菜園日誌,記錄採收日期,也結算冬耕成績。西蘭花總算炒出一盤,蜿豆苗和捲心萵苣被鳥吃,齒葉萵苣發育遲鈍,天暖後才猛長,但菜味已苦韌,也算失收。怪了,去年的萵筍也槓龜,為什麼我老是種不成萵苣?可能是肥力問題,得再檢討。
芹菜則是敗部復活,異軍突起。十一月底栽苗,一月中還矮矮瘦瘦,莖桿泛出紫褐,查了書,才知道澆水不夠,趕快補救。立春後,芹梗終於有點抽高,還是不成材,送我菜苗的文蒂,早就採了好幾回,人家的芹菜高壯及膝,玉綠水嫩,我的看來還像大芫荽。
但二月中旬雨水後,這菜好像睡醒了,急起直追,逐日粗長,梗管青碧挺拔,枝葉翠意婆娑,到月底已可以採收。芹菜不像西蘭花般易老,不趕著收,我想到就去拔幾棵,拿來煎芹香蛋,炒肉絲豆乾,切珠撒海鮮粥,煮麵和炒米粉。因為晚熟,這芹菜粗矮多節,並不脆嫩,然而滋味鮮濃,有種特別的藥香,連嫩葉都可入饌。吃到現在還有半畦,莖節開始抽花,馨馥更甚,我打算採來包餃子。
芫荽也不錯,年底撒籽,立春後長到食指高,驚蟄後開始可採。韭菜和紅菜,都是前兩季留下來的,冬天無精打采,入春後逐漸豐肥,韭菜變寬拉長,紅菜圓闊光潤,吃來柔美生脆,滿口春味。還有些香辛菜,辣椒、蒜苗、蒔蘿和義大利芹菜,下星期應該也能採。這些菜都粗生易養,又不招蟲惹鳥,挺適合我的耕種水平。
噪鵑已回到了南方,在樹上哇哇叫,歪著頭看我耕田。我把採收後的根莖殘株,連同剛揀的芹菜葉,搗碎之後一併送做堆,埋入深處做綠肥。下一季,田土裡的綠色精魂,就像噪鵑一樣,還會回來。
我好土
芒果和檸檬在開花,甜馥芬馨,惹來粉蝶翩翩,蜜蜂嗡嗡,連土裡也有春意,揮鋤下地,覺得豐厚綿軟,土粒鬆爽如糕粉,不時翻出蚯蚓,精壯生猛,活蹦亂跳。
這可是寶啊,活土才有蚯蚓,得來不易,以前沒有哩。我一直以為,菜田石塊太多,土質磽惡,但有個做營建的朋友來看了,搖頭說,不是土質問題,妳這田根本不是天然地,是堆填地,用建築廢料填高,鋪上泥土擴充出來的。
我聽了,如雷轟頂,但也恍然大悟,原來是塊惡土,難怪層層相疊,有挖不完的殘垣斷壁,堅硬枯瘠,再怎麼下肥也瘦巴巴。早知就徹底換土,害我胼手胝足,幹了大半年,搞得磨繭起泡,勞筋折腰,土性低劣難移,恐怕白忙一場。
懊惱失望,氣苦不已,但轉念一想,這地好歹收過幾季瓜菜,並非一毛不拔,況且耕耘了大半年,日夕沾碰撫弄,已經有感情,也不忍心清除鏟走。再說,鏟走了能丟到哪裡?還不是送去掩埋堆填,滋生更多廢地荒原。我一直很內疚,前年裝修房子,拆牆敲磚的,不知製造幾噸建築廢料,造孽不少,把這塊廢地整治好,就算贖罪吧。
我不知試過多少施肥法。堆肥惹蟲蠅,漚肥太少也太慢,草葉灰沒有氮,不夠營養;又因土面虛不受補,買來的肥料成效不彰,吸收遲緩。地上行不通,索性走地下路線,改用最原始的「掩埋施肥法」,把廚餘直接埋在田底,再輔以落葉草木灰。這招好像管用,幾星期後,菜漸漸肥了。
屢敗屢戰,土改終於有進展,我樂得手舞足蹈──哎喲,不行,只能足蹈,手臂勞動過度,痛得要去看跌打,舞不了。但我逐漸掌握土性,知道菜田變肥,在虛不在實,不是因為下好料、埋了仙丹大補丸,是因為結構改善,土層有腐殖質,開始鬆動軟化。
我更加勤奮,每天刨坑挖洞,掘出磊磊磚石,搗碎硬塊和黏土後,倒入果皮菜葉,澆水覆蓋掩埋……,還好,菜地不全都是堆填,深層仍然有藤黃色的真土,黏稠緊實如年糕,要鏟鬆切細,拌入砂礫草灰,讓土壤有毛管孔隙,可以呼吸透水,微生物才能做工夫,滋育營養肥力。
一點點,一塊塊,地毯式掘過來,進度雖慢,成果斐然,芹菜和青蒜長粗了,韭菜葉由窄變闊,寬柔如飄帶,吃起來鮮嫩有甜味。紅鳳菜發福,比以前胖了一倍,莖幹像蔓藤伸到籬外,摘也摘不完。義大利香芹原本呆滯,細瘦如野草,現在茂密高壯,碧骨翠葉,做沙拉和Pasta鮮香濃馥,長得太快吃不完,還得送人。
對照很明顯,另一邊的芫荽還沒埋肥,生得矮細,老早就抽花。原來土性如人性,不能以本質論斷,要加以涵養改良,然則人性複雜,叵變難測,不像土性忠實簡單,用對方法下足功夫,就能扭轉頑冥惡地,化腐朽為神奇。
春來整地,蚯蚓活潑扭動,土層生出黑沃腐質,泥土觸感也不同,鬆柔而又油潤,隱隱有勃鬱生機,果真是「陽氣俱烝,土膏其動」,天候暖熱,催發土壤作用,肥力流動播散,我甚至聞到地氣,是一種微微的煮豆香。
土壤是神奇之事,書上說,一公分深的土壤,地球要花三百年形成,而能種植的「有效土壤」,則需三十公分以上。哇,那不就是九千年,我還得加油吶。
嫁果子
繁花落盡,芒果凝出青豆小果,我每早去給「湯米」加油,叫它站穩別掉。茉莉開出星點白花,清芬沾衣,我深深呼吸,喃喃讚歎。雞蛋花抽新芽,木芙蓉長出嫩葉,當然也要鼓勵一下。
桃樹有蚜蟲,我警告蟲子快滾,不然殺無赦。鋤地砍到蚯蚓,趕緊跟牠道歉,哎哎對不起,被腰斬一定很痛吧。水蜈蚣在草地橫行霸道,貪婪瘋長,我一邊拔一邊罵。種地一點也不孤寂,你看我多吵,不是罵罵咧咧,就是嘟嘟噥噥。據說跟植物講話,它能領略感應,我不信鬼神,卻相信超自然,在園子裡於是喋喋不休,努力跟草木蟲鳥溝通。
迷信是原始的心智,錯認的因果關聯,不只人類,動物也會,我看過紀錄片,說科學家做實驗,發現鴿子也迷信,以為繞圈哈腰做些動作,就會得到食物。但凡人力(以及鴿力)不能駕馭之事,迷信就會滋生,耕種涉及自然,日月天候品種土壤,有千萬因素交互影響,更是迷信的溫床,人類種地幾千年,到現在還拿天氣沒辦法,很多事都得「望天打卦」,古人想必更加迷惘。
翻閱古代筆記和農書,種植迷信奇想聯翩,妙趣橫生,譬如宋代的《證類本草》說,「胡麻須夫婦同種,即茂盛。」明代的《群芳譜》說,種桃時把桃核刷淨,「令女子豔粧種之,他日花豔而子離核。」又說,桃樹蛀了,就用豬頭煮湯,放冷後澆灌。
歷代《本草》雖是醫書,也多奇談異志,譬如說,把一小片鱉甲裹上莧菜,放入土坑,「一宿盡變成鱉也」,這倒好,種菜得鱉。南朝的《異苑》則說,挖薯蕷(山藥)不能出聲,「嘿然則穫,唱名便不可得」,我這麼碎碎唸,看來不能種山藥。
果樹最多種植迷信,譬如自古相傳,「橘見屍則多實,榴得骸而葉茂」,元朝的《農桑通訣》、明代的《種樹書》和《便民圖纂》都說,在橘樹根下埋鼠屍,在石榴枝杈安放枯骨,就能結實繁茂。清初陳淏子的園藝書《花鏡》,則提及嫁李和嫁杏,嫁李要在「元旦五更,將火把四面照看」,即可結子纍纍。嫁杏就鄭重些,要在樹枝繫上處女穿過的紅裙,並以酒祝禱。
唐人段成式的筆記《酉陽雜俎》,亦有「嫁茄子」,說是茄子開花時,把茄葉摘下散佈路上,撒上灰讓人踐踏,結實即繁。最妙的是李漁,他的《閒情偶寄》說,合歡樹要澆洗澡水,「常以男女同浴之水,隔一宿而澆其根,則花之芳妍較常加倍。」這是他親身種植的經驗哩。
南北朝的農書經典《齊民要術》,也有「嫁棗」,說正月初一日出時,用斧背在樹幹槌擊敲打,可使棗樹結果豐盛。這個嫁,卻和嫁李子嫁茄子不同,可就有道理了。原來,以斧或杵敲打樹幹,擊傷果樹韌皮,可以阻止養分向下輸送,促進開花結果,古時的農書叫「嫁果」,現在叫「環剝法」。
種植迷信是古老的交感巫術,擬人化的推論和想像,以今觀古,猶如高處望低,我們不免嗤笑,以為無知無稽,然換個角度看,這何嘗不是民胞物與,天人合一?人類生涯短淺,所知有限,很多事尚未洞悉明理,只可存而不論。
所以近代西方,有人提倡「自然活力農耕」(Bio-dynamic Agriculture),認為土壤除了天然條件,還受農人的意志精神,月亮,以及其他星球的力量影響。另有一派更激進,主張萬物有靈,山水草木各有精靈,耕地種植,須與精靈互通共處。
哎,這我就不信了,因為除了草木蟲鳥,還得要跟山鬼水神、各方精靈溝通交談,忙不過來啊。(本文摘自《種地書》第一輯「傻婆荷蘭豆」。小標由蔡珠兒親筆手寫。整理摘錄:編輯部)
書籍簡介_種地書
作者:蔡珠兒
出版日期:2012.3.1
出版社:有鹿文化
小檔案_蔡珠兒
台灣作家、南投埔里人。英國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系研究所畢業,曾任《中國時報》資深記者。現居香港,著有《南方絳雪》、《雲吞城市》、《紅燜廚娘》等書。